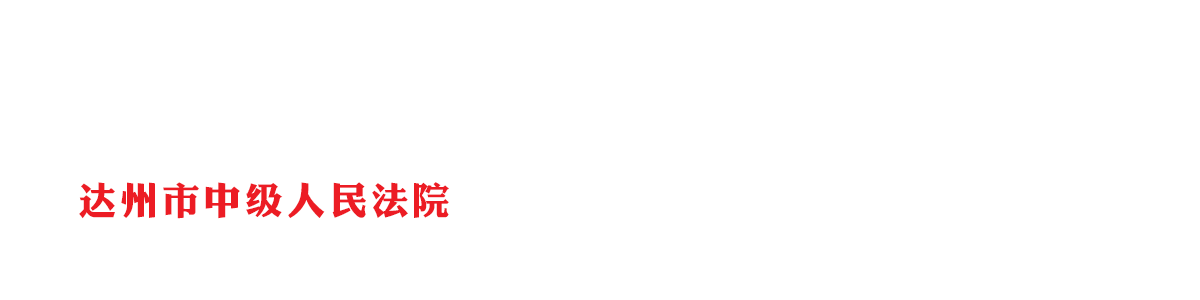一、问题的提出
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是指在公共道路上设置妨碍通行物,致使他人人身或财产遭受损失,根据相关法律规定,(1)有关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其中“有关单位”包括道路管理者。道路管理部门之所以构成侵权,承担侵权责任,在于道路管理部门的消极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堆放、倾倒、遗撒行为偶然结合,造成损害结果的发生。道路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并未直接或必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而是为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直接侵权行为提供了机会或条件,道路管理者应属于民事侵权责任主体。此外,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妨碍通行致害事故,受害人与高速公路管理者之间通常存在收费合同关系,高速公路管理者未及时履行清理义务构成违约行为,同时其不作为也构成侵权行为,这就构成了违约责任与侵权责任的竞合。现实生活中,在高速公路上发生妨碍通行致害事故,往往会严重侵害受害人的生命健康,受害人为了获得精神损害赔偿,通常会选择侵权责任予以救济,很少采取违约责任。本文探讨的是妨碍通行致害中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不探讨违约责任问题。关于《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的“侵权责任”以及《解释》第10条规定的“相应的赔偿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2),司法实践中主要有以下几种判决:
案号 | 法院裁判 | |
按份责任 | (2015)长民二终字第236号 | 法院认为,上诉人作为道路管理者承担的相应责任来源于未及时清理遗撒物,系消极的不作为,是损害发生的次要原因。上诉人承担“相应责任”为按份责任而非连带责任。 |
(2013)田民一初字第03246号 | 法院认为,依法以50%的按份责任,由被告淮南市市政管理处承担公共道路管理瑕疵行为的侵权责任较妥。 | |
(2017)鲁0323民初3022号 | 法院认为,本案案由为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害责任纠纷,法律规定对于公共道路妨碍通行致害责任纠纷的责任主体,确立了不同的归责原则,道路管理部门依照法律规定承担按份责任。 | |
相应的补充责任 |
| 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第70条规定公路管理机构负有管理和保护公路的责任,公路局作为涉案道路的管理人,应当对本案涉案道路承担管理责任,确保道路安全畅通,公路局作为公路的管理责任主体,对在正常通行的道路上擅自堆放沙子的行为未采取任何措施,未完全尽到管理责任,与事故的发生有一定的因果关系,亦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
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
(2016)渝04民终617号 | 法院认为: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行为人和公共道路管理之间对受害人形成不真正连带责任之债。而事故的终局责任者是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物品的行为人,如果公路管理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则可向实施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人追偿。 |
二、对法院判决的评析
司法实践中之所以存在以上三种判决,原因在于法院对道路管理者侵权责任主体性质认识不同,所适用的法律不同。
(一)对法院判决承担按份责任的分析
针对法院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认为道路管理者承担按份责任,笔者不赞同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全国人大法工委指出,《侵权责任法》第8条、第11条、第12条之间是依次适用的关系。(3)首先,看行为人与道路管理者是否满足第8条共同侵权,《侵权责任法》第8条共同侵权仅限于有意思联络的共同侵权,(4)共同侵权应以意思联络、共同过错为必要条件,道路管理部门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通常不存在意思联络、共同过错,即道路管理部门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不构成共同侵权,不承担连带责任。陕县城市管理局与张丽艳、李智顺、李廷彦、罗秋梅、张矿良、胡志明、陕县交通运输局、陕县公路管理局、原审被告陕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公共道路妨碍通行损害责任纠纷案,(5)法院认为:“因行为人和道路管理部门之间并无意思联络,只是因偶然因素使无意思联络人的行为偶然结合而造成本案损害结果的发生,故各原审被告不具备共同过错。”道路管理部门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属于无意思联络的混合侵权,即道路管理部门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之间不存在共同的过错、意思联络,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条。
其次,看行为人与道路管理者是否满足《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构成要件。《侵权责任法》第11条为叠加的分别侵权行为,即:每一个行为人实施的侵权行为对损害后果的发生都具有百分之百的原因力,去掉其中任何一个行为人的侵权行为,损害后果依然发生,则各个侵权行为人承担的是连带责任。(6)针对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的“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指出,各侵权人的行为均为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7)司法实践中,法院也认为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前提是二人以上的加害行为都是造成侵害后果的直接原因。(8)对于原因力适用,主流观点是区分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直接原因是指必然引起某种损害后果发生的原因,一般直接作用于损害后果,即没有介入其他人的行为而直接引起结果的发生,并且,直接原因必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即它在损害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表现出某种必然的、确定的趋向。(9)间接原因通常不会直接引起特定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损害结果之间没有直接的、必然的联系,但由于其他原因(如第三人的行为或受害人自身因素)的偶然介入,并与这些因素相结合,才产生了损害后果,它对损害的发生起到了加力的作用。(10)显然,道路管理部门的不作为并未直接或必然导致损害结果的发生,与损害后果之间无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满足《侵权责任法》第11条的构成要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条。
最后,看是否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针对《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指出,每一侵权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11)梁慧星老师也持此观点。(12)司法实践中,法院也认为《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是指“每一侵权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比如泛诚(福州)物业管理有限公司与廖尚培等财产损害赔偿纠纷上诉案,(13)二审法院认为:“殊不知该法条(《侵权责任法》第12条)是关于无意思联络数人竞合侵权行为的规定,其构成要件为每一侵权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而本案实施加害行为的第三人与未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人是一种积极的作为行为与一种消极的不作为行为的竞合,显然原判存在适用法律错误,应予纠正。”《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是指每一侵权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道路管理部门的消极不作为显然不符合《侵权责任法》第12条的构成要件,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不承担按份责任。
(二)对法院判决承担补充责任的分析
针对法院认为根据《侵权责任法》第37条之规定,道路管理者属于“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当承担安全保障的注意义务。道路管理者对妨碍通行致害责任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的“公共道路”是否属于“公共场所”,是认定对道路管理者能否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关键,如何理解《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公共场所”,《现代汉语词典》中“公共”是指:“属于社会的,公有公用的。”(14)“公共场所”是指属于社会的、公用的地方。“公共道路”当然属于社会的、公用的地方,属于“公共场所”。并且道路管理者在客观事实上扮演着“管理者”的角色,属于《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公共场所的管理人”,应当承担安全保障义务。
道路管理者承担安全保障义务是“中等程度”或“合理的”注意义务。理由如下:第一,道路管理者既然是从事较高专业性、技术性的管理活动,其注意程度自然高于一般常人。第二,高速公路的管理者进行收费,提供的是有偿的服务,按照利益与风险一体化思想,收益和风险总是同在,道路管理者既然从中获取利益,就应承担一定的风险,收益是风险的回报,风险是收益的代价,道路管理者自然要承担安全保障义务。第三,从避免损失发生的成本来看,道路管理者承担安全保障的义务,对妨碍通行物事先清理可以节约成本,如果要求行人事先清理,行人为此要付出高昂的成本,此种做法很不经济、不方便。况且道路管理者通常具备清理的能力,对道路管理者而言,成本低廉、操作方便,实属举手之劳。第四,通常,发生损害的危险性越大,则要求的谨慎和勤勉程度越高,在涉及人的生命、健康和公共安全的场合,存在着更高的注意要求。(15)在公共道路上妨碍通行关乎社会公共利益,关乎不特定多数人的生命健康安全,道路管理者理应对此负有更高的注意义务,确保公共道路的安全、无危险,为社会公众营造一个安全可靠的道路交通环境,也有利于强化道路管理部门的社会责任感。
本文认为道路管理部门违反安全保障义务,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第一,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属于直接侵权,道路管理部门属于间接侵权。从原因力的角度分析,对损害事实的发生,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负直接的、主要的原因,道路管理者负间接的、次要的原因,从过错程度的角度分析,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过错程度较大。第二,行为人作为第一顺序责任人,道路管理者是第二顺序责任人,在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有能力赔偿的情况下,道路管理者无需赔偿。在无法找到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或者行为人无经济能力承担赔偿的情形下,受害人又无法通过国家赔偿得到救济,此时基于公共政策的考量,为了确保受害人能够得到及时的救助,让受害人可以向距离更近、更具有赔偿能力、更容易行使权利的道路管理者索赔,在此情形下,要求道路管理部门承担补充责任,不仅有利于受害人获得及时的救济,也有利于督促道路管理者积极履行清理义务,保障道路公共安全。第三,“相应的补充责任”是在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的情况下,根据补充责任人的过错与原因力大小承担有限的补充,并未过分加重道路管理者的经济负担。第四,为了防止对道路管理者不公平,打消道路管理者的积极性,允许道路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后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行使追偿权。
道路管理者作为安全保障义务人,对道路管理者既能适用《侵权责任法》第89条,也能适用第37条。笔者认为,就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形态认定而言,《侵权责任法》第37条与第89条构成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侵权责任法》第37条属于一般法,《侵权责任法》第89条属于特别法,由于第89条规定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不明确,应适用一般法《侵权责任法》第37条规定的“相应的补充责任”,补充责任属于特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三、道路管理者侵权责任形态理论解析
(一)学界争议
关于妨碍通行致害中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形态,学术界有以下六种观点:
1.按份责任说
分别侵权行为所对应的责任形态应是按份责任,故道路管理者在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中应承担按份责任。(16)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和道路管理者应当向受害人承担按份责任。(17)该说认为道路管理者不作为符合《侵权责任法》第12条规定的“分别侵权行为”,应承担按份责任。
2.补充责任说
道路管理者的责任承担上采取何种方式,可以借鉴《侵权责任法》第37条的规定。(18)该说从安全保障义务的角度出发,认为道路管理者不作为属于违反安全保障义务,应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3.不真正连带责任说
杨立新教授持此观点。(19)该说认为行为人的直接侵权行为与道路管理者的间接侵权行为结合在一起,最终造成了损害结果的发生,即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道路管理部门应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4.按份责任抑或补充责任说
道路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抑或按份责任,要具体分析第三人和管理者的主观状态。当第三人主观上是过失时,管理者承担按份责任。其他情形下,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20)即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形态不是唯一的,既可能是按份责任,又可能是补充责任,应结合第三人和管理者的主观状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5.补充责任抑或连带责任说
邓瑞平教授认为道路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抑或连带责任,第一,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作为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适用《侵权责任法》第37条第2款,道路管理者承担补充责任;第二,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不作为共同导致损害结果发生,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1条,道路管理者承担连带责任。(21)该说结合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作为抑或不作为,对道路管理者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侵权责任形态进行类型化。但王利明教授对此指出,它不是连带责任,凡是法律规定承担连带责任的,应当设置明确的规则。如果要求公共道路的所有人或管理人(如市政管理者、城市环卫部门等)承担连带责任,显然会不当加重其责任。(22)
6.国家赔偿责任说
尽管我国的《国家赔偿法》并未将道路管理瑕疵责任列入国家赔偿的责任之中,但无论是从保护受害人的角度,还是从国际立法趋势,或是我国立法实践上考虑,都应当将道路管理瑕疵责任纳入国家赔偿范围。(23)该观点建议我国《国家赔偿法》未来修改中将公有公共设施致害赔偿纳入国家赔偿的范围。
(二)道路管理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
本文认为道路管理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24)《民法总则》没有规定不真正连带责任,但在多数人民事责任体系中不能缺少这种责任形态。(25)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按照从行为对主行为所发挥作用的大小不同,可分为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与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对于如何判断加害人行为是否为损害结果发生的必要条件,各国的理论与实践依据加害人的行为是作为抑或不作为加以区别,其判断方法可以分为“剔除法”与“替代法”,一是积极作为情形下的“剔除法”,在作为侵权中,通常采用剔除法认定因果关系;二是消极不作为情形下的“替代法”,被告的行为系不作为时,应采取替代法。(26)根据“替代法”基本原理,将道路管理部门不作为替换成作为,可能出现的结果可分为以下三种情形:第一,如果道路管理部门依法积极履行法定职责,损害结果仍不可避免,比如利用现有的科学技术根本无法清理妨碍通行物,说明道路管理部门不作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道路管理部门不承担侵权责任。第二,如果道路管理部门依法积极履行法定职责,能够完全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比如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完全可以清理妨碍通行物,此种情况下,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道路管理部门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第三,如果道路管理部门依法履行法定职责,损害后果仍会发生,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受害人的损失,比如利用现有的技术设备无法完全清理或者只能部分清理妨碍通行物,此时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道路管理部门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详见下文分析。
1.道路管理者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
道路上,当第三人实施了堆放、倾倒、遗撒妨碍物造成他人损害时,作为提供“机会”的道路管理者,应当根据自己的过错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27)即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28)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29)“相应的”是立法者刻意地、有目地加上去的,“相应的”是对补充责任的限制,如果去掉“相应的”意味着“缺多少补多少”,可以全额补充,即完全的补充责任,立法者加上“相应的”是要与完全的补充责任相区别开来。
“相应的”的责任范围应结合道路管理者的过错程度、原因力大小(30)综合判定。对损害结果的发生,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构成直接侵权,负直接的、主要的原因;道路管理者构成间接侵权,负间接的、次要的原因,从过错程度的角度分析,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的过错程度通常大于道路管理者。因此,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负主要责任,道路管理部门负次要责任。
全部责任+补充责任,是指在两个主体均对损害后果负有责任的情况下,将二者区分为主要责任人(直接侵权人)和补充责任人。在主要责任人有能力承担全部责任的情况下,补充责任人无须承担责任。(31)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道路管理者分别作为第一顺位、第二顺位的侵权责任人,道路管理者对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享有先诉抗辩权。至于补充责任人承担补充责任之后是否享有对第一责任人的追偿权,《侵权责任法》并未作出规定,有学者认为,我国《侵权责任法》规定的相应的补充责任是补充责任人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损害负责,本质上是一种自负的过错责任,因此,补充责任人在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后不能再向实际加害人追偿。(32)但从最高人民法院两份现行有效的司法解释(33)来看,补充责任人享有追偿权,即应允许这种偶然结合的侵权行为人之间行使追偿权,道路管理者承担了相应的补充责任后,可以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行使追偿权。
综上所述,“相应的”补充责任对受害人而言可能只是杯水车薪,甚至仅是象征性的补偿,若受害人无法通过侵权损害赔偿的途径获得充分地救济,可能会引发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从构建和谐社会的角度出发,在妨碍通行致害侵权领域有必要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以侵权责任为基础,以责任保险、社会救助为辅助,弥补单纯依靠侵权损害赔偿的不足。王利明教授指出,有必要通过不断扩大责任保险的适用范围,不断增强社会救助的功能,与侵权法协同发挥对受害人全面有效救济的作用。(34)
2.道路管理者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
如果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35)道路管理部门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道路管理者属于中间责任人,行为人是最终责任人。受害人可以选择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与道路管理部门一个或两个请求赔偿,道路管理部门与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都有义务承担全部赔偿责任,道路管理部门向被侵权人作出赔偿之后,有权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全额追偿,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承担的赔偿责任为最终责任,无权向道路管理部门追偿,即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承担的最终责任份额为100%。
结语
关于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形态,首先,道路管理者不承担连带责任。其次,道路管理部门的消极不作为不适用《侵权责任法》第12条,道路管理者也不承担按份责任。本文赞成道路管理者承担不真正连带责任,按照替代法原理,将道路管理部门不作为替换为作为,如果能完全避免损害结果的发生,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道路管理部门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道路管理部门作出赔偿后,有权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全额追偿,即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作为最终责任人;同理,将道路管理部门不作为替换成作为,即道路管理部门依法积极履行法定职责,尽管不可避免损害后果的发生,但能够在一定范围内减少受害人的损失,道路管理者的不作为与行为人堆放、倾倒、遗撒的行为构成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道路管理部门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并且道路管理者可以向妨碍道路通行行为人行使追偿权。
(1)《侵权责任法》第89条规定:“在公共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妨碍通行的物品造成他人损害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0条规定:“因在道路上堆放、倾倒、遗撒物品等妨碍通行的行为,导致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请求行为人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道路管理者不能证明已按照法律、法规、规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者地方标准尽到清理、防护、警示等义务的,应当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2)侵权责任形态是指侵权法律关系的当事人所承担侵权责任的不同表现形式。侵权责任形态所研究的内容,就是侵权责任在不同的当事人之间的分配。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原理与案例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第195-197页。
(3)全国人大法工委指出,在处理数人实施侵权行为的具体案件时,首先需要看是否满足第8条共同侵权制度规定的构成要件;不符合的,看其是否满足本法第11条的构成要件;也不符合的,再看其能否适用本条(第12条)规定。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
(4)全国人大法工委指出,共同侵权行为中的“共同”主要包括三层含义:其一,共同故意;其二,共同过失;其三,故意行为与过失行为相结合。参见王胜明:《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释义》,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第64页。
(5)参见河南省三门峡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三民终字第652号民事判决书。
(6)参见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2015)苏商再提字第00076号民事判决书。
(7)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93页。
(8)参见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17)川民再480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二人以上分别实施分割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适用的前提是二人以上的加害行为都是造成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江苏省徐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苏03民终446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结合王光良的尸检报告内容可以看出,无论是杨波的撞击行为还是赵长明的碾压行为均是王光亮死亡的直接原因,也就是说,赵长明及杨波的加害行为均足以造成王光亮死亡后果的发生,原审法院据此依照《侵权责任法》第11条规定判令赵长明与杨波对受害人王光亮死亡造成的全部损失承担连带责任于法有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7)渝01民终4635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11条强调的是各个独立的行为均足以造成全部损害,即各侵权人的行为均为发生损害后果的直接原因。” 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2015)成民终字第6744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11条关于‘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害行为造成同一损害,每个人的侵权行为都足以造成全部损害的,行为人承担连带责任’的规定,适用的前提是二人以上的加害行为都是造成侵害后果的直接原因。”
(9)参见江苏省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8)苏09民终4092号民事判决书。
(10)参见湖北省高级人民法院(2018)鄂民终48号民事判决书。
(11)参见最高人民法院侵权责任法研究小组:《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条文理解与适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6年版,第96页。
(12)梁慧星教授指出,民法上所谓“行为”有“积极行为”(“作为”)与“消极行为”(“不作为”)之别。《侵权责任法》第12条所谓“行为”,仅指“积极行为”(“作为”),而不包括“消极行为”(“不作为”)。参见梁慧星:《共同危险行为与原因竞合》,载《法学论坛》2010年第2期,第6页。
(13)参见福建省三明市中级人民法院(2017)闽04民终300号民事判决书。类似的案例:湖南省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岳中民一终字第481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规定的‘二人以上分别实施侵权行为’是指每一侵权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 江苏省扬州市中级人民法院(2014)扬民终字第0387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殷海剑和何春香的行为都独立具备构成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且二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属于竞合侵权行为,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按份责任。”江苏省无锡市滨湖区人民法院(2015)锡滨民初字第00438号民事判决书,法院认为:“周锋和马琪渊的行为都独立具备构成侵权行为的全部要件,且二人的行为都是作为行为,属于竞合侵权行为,应适用《侵权责任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承担按份责任。”
(14)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2年版,第450页。
(15)参见王卫国:《民法》,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515页。
(16)参见尹相彬:《妨碍通行物致害责任中道路管理者侵权责任研究》,延边大学2017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7页。
(17)参见杨会:《论道路管理者侵权责任的承担》,载《法学杂志》2019年第2期,第93页。
(18)参见董思航:《论妨碍通行物损害中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
(19)杨立新教授指出,道路管理者承担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其基础是这种行为是竞合侵权行为,承担责任的侵权人又为两方,适用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可谓恰如其分,高速公路管理者承担妨碍通行物损害责任,应当适用典型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参见杨立新,李佳伦:《高速公路管理者对妨碍通行物损害的侵权责任》,载《社会科学战线》2013年第9期,第158页。
(20)参见张平:《妨碍通行物致害中公共道路管理者民事责任研究》,华中师范大学2018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9页。
(21)参见邓瑞平、董威颉:《道路管理者数人侵权案件侵权责任形态研究》,载《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1期,第34页。
(22)参见王利明:《侵权责任法研究》(上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727页。
(23)参见赵丹:《公共道路妨碍通行物损害责任责任探析》,西南政法大学2015年硕士学位论文,第25页。
(24)不真正连带责任,也称为不真正连带债务,是民法理论中的一种重要的债务形式,在侵权责任法领域叫作不真正连带责任。侵权法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是指多数行为人违反法定义务,对一个受害人实施加害行为,或者不同的行为人基于不同的行为而致使受害人的权利受到损害,各个行为人产生的同一内容的侵权责任,各负全部赔偿责任,并因行为人之一的履行而使全体责任人的责任归于消灭,或者依照特别规定多数责任人均应当承担责任的侵权责任形态。参见王利明:《民法学》,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956页。
(25)参见杨立新:《民法总则》,法律出版社2017年版,第285页。
(26)参见韩强:《法律因果关系理论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27)参见董思航:《论妨碍通行物损害中道路管理者的侵权责任》,吉林大学2016年硕士学位论文,第19页。
(28)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是指两个竞合的行为,从行为为主行为的实施提供了机会,使主行为的实施能够顺利完成的竞合侵权行为。提供机会的竞合侵权行为的法律后果是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即有限的补充责任。补充责任也是不真正连带责任的一种变形,是特殊的不真正连带责任。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北京大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100页。
(29)相应的补充责任,是指直接责任人不能承担赔偿责任或者不能完全承担赔偿责任,补充责任人按照其过错程度或者行为的原因力,承担相应的补充责任的补充责任形态。这种补充责任不是全部补充而是有限补充,以此叫做有限的补充责任,这种有限的补充责任在《侵权责任法》中叫做相应的补充责任。参见杨立新:《侵权法论》,人民法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756页。
(30)原因力,是指在引起同一损害结果的数个原因中,每个原因对于该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挥的作用力,原因力理论适用于多因情况下各行为人侵权责任份额的承担或赔偿义务人与受害人之间对损害后果的分担。一般说来,其行为原因力大的,承担更多份额的赔偿份额,反之则承担较少份额的赔偿份额。比较行为人行为的原因力通常与比较当事人之间的过错结合运用,以最后确定责任分配。参见张新宝:《侵权责任法原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72页。
(31)参见王利明:《民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623页。
(32)参见王利明、周友军、高圣平:《中国侵权责任法教程》,人民法院出版社2010年版,第37页。
(33)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铁路运输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3条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第2款。
(34)参见王利明:《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受害人救济机制》,载《中国法学》2009年第4期,第152页。
(35)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是指两个行为中的从行为(即间接侵权行为)与主行为(即直接侵权行为)竞合的方式,是从行为为主行为的实施提供了必要条件,没有从行为的实施则主行为不能造成损害后果的竞合侵权行为。换言之,间接侵权人的从行为是直接侵权人的主行为完成的必要条件,这种竞合侵权行为就是提供条件的竞合侵权行为。参见杨立新:《侵权责任法》,复旦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54页。